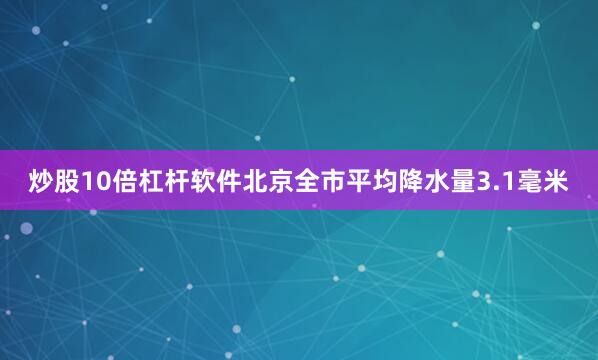股票配资操作隋朝开凿的大运河诸段

古人给一个地方命名,最基础、最普遍的原则是以地形地貌来确定,如果一地遍布沙丘,其名字很大概率可能就叫“沙丘”了。今天以“沙丘”为名的地方已经不见,但是历史上有几个“沙丘”知名度却非常高。

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位于今天河北省广宗县的“沙丘宫”或“沙丘平台”,它之所以有名,是因为它有三大赫赫“战绩”:1、商纣王在这里筑台,蓄养禽兽、“大聚乐戏”,以至于身亡并失国;2、公元前295年,赵武灵王被公子成及李兑所围,饿死在了这里;3、公元前210年,秦始皇在巡视途中病死于这里。所以它成为后世历代帝王避之不及的“困龙之地”。

此外,在历史上还曾出现过“沙丘县”,在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中均有记载。《旧唐书》:“武德五年,置毛州,割魏州之馆陶、冠氏、堂邑,贝州之临清、清水。又分置沙丘县。贞观元年,废毛州,省沙丘、清水二县……”《新唐书》:“武德五年,以馆陶、冠氏及博州之堂邑,贝州之临清、清水置毛州,并析临清置沙丘县。贞观元年州废,省清水入冠氏,省沙丘入临清,余县皆还故属。”
2025年6月,临西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:《新见唐〈万仁则墓志〉与沙丘城研究》,文中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于河北省邯郸市邱县香城固村北的一处土坑中出土了唐《万仁则墓志》,墓志提到“合葬于沙丘城列市之北三里”,由墓志出土位置与墓志所载,可证明今天邱县香城固就是唐朝曾作为沙丘县治所的沙丘城。

墓志的末尾,还引用了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:
我来竟何事,高卧沙丘城。城边有古树,日夕连秋声。鲁酒不可醉,齐歌空复情。思君若济水,浩荡寄南征。
有意思的事情来了,墓志里这首诗中“思君若济水”句与大家所熟知的、诸多古籍中所记载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“思君若汶水”句,有“济水”与“汶水”的差异。
从墓志中记载的“大历元年(766年)十一月十日,与夫人合葬于沙丘城列市之北三里”,可以推断该墓志铭撰写时间,这个时间与天宝四载(745年)创作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一诗中间仅相隔21年,可以说墓志里的这首诗,或许就是作者原诗最初的模样。
那么,既然由墓志可以得出邱县香城固就是唐朝沙丘县治所沙丘城的结论,是不是也说明诗里的“沙丘”就是这里呢?
关于这一点,笔者认为需要慎重:虽然唐朝的沙丘城与李白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同时出现在了同一块墓志铭碑文上,但就这么说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中的“沙丘”就是今天的邱县香城固,有些牵强和武断了。
理由有以下四点:
一、从诗中提到的几个元素来看,李白诗里的“沙丘”显然不是在说香城固及其周边。
诗中“鲁酒不可醉,齐歌空复情”的“鲁酒”与“齐歌”两个元素,表明“沙丘”应该位于有着浓厚的、春秋战国时期鲁地、齐地文化交汇气息的地方。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,李白诗歌才能以“鲁酒”“齐歌”来作为自己对杜甫思念之情输出的替代品。地理位置稍偏一点、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少一点的地方就无法替代,这种情绪都无法得到圆满表达和释放。那么,香城固一带能达到这个条件吗?

有人说,今天的山东省往往称“齐鲁大地”,显然说齐鲁就是说山东省。邱县在明清曾属于山东省,沙丘县是也是由在明清同属山东省的临清析置而来,难道香城固和“鲁酒”“齐歌”两个元素不能够联系起来吗?
其实,临清、邱县一带属于今天山东区域内管辖是在元朝之后了,距今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,在那之前一直属于燕赵文化圈。就连编修于清朝的《邱县志》《临清州志》中对两地所处的地理及人文环境的描述里,涉及山东或者齐鲁的因素也是偏少。

比如《邱县志》的《星野》《序》里分别说邱县:“……邱古乾侯,属晋赵,总隶冀州域……”“邱邑僻处东省西陲”。
而《临清州志》《序》《风俗》《星野》分别说临清:“北控燕赵、东接齐鲁、南界魏博、河运直抵京师,水陆交冲,畿南一大都会”“……今之郡县古之列国也,披阅舆图,州于列国为赵为卫,故其人多慷慨好义……”“……临清古兖冀之交……”
由此可以看出,即便是在行政区划上已归属于山东管辖数百年之后的清朝,在描述它们所处地理文化环境时,齐、鲁元素仍然不算太多,更不论比元朝要早500多年的唐朝了。
虽然不知道在唐朝以什么样的词汇来称呼香城固一带的风土人情,但绝不应该是“鲁酒”“齐歌”。
二、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诗中所说的“济水”是永济渠吗?
网络搜索关键词《万仁则墓志》,发现与之相关的除了本文开篇时所说文章之外,还有其他两篇,在这三篇文章内或以确定的语气、或以不确定语气,均指出“思君若济水”一句中的“济水”就是流经沙丘城东部、开凿于隋朝的大运河“永济渠”,并且称永济渠是唐朝的南北大动脉、高速公路……

其实,今天的人们认识到永济渠的重要,是在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之后,朝廷依托隋唐永济渠构建了黄河以北的漕运大动脉才形成的。而在唐朝,隋朝开凿的大运河诸段,仅是黄河以南的通济渠等河段,因联系京城与江南富庶之地,人员物资往来络绎不绝,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才能够凸显出来的,白居易所写的《长相思》中“汴水流、泗水流”中的“汴水”就是指的是通济渠。特别是皮日休对隋炀帝及大运河的评论诗《汴河怀古》也是说的是汴河: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?”

而永济渠,仅在唐初用来向北方边境地区运送军用物资,有限的与经济相关动作也就是高宗、玄宗朝在沙丘城以南近二百里的魏州,疏通渠道、开魏州西渠“控引商旅”“贮江淮之货”,根本辐射不到沙丘。安史之乱后,永济渠近乎全河段陷入藩镇割据之下,运道断绝、商旅不兴。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,唐朝诗人几乎无人创作有关描写“永济渠”的诗歌,这一情况经过deepseek的搜索分析得以验证。
相对于名声沉寂的永济渠,“济水”的名字却可以说是相当的响亮!
“济水”是在古人认知里同长江、黄河、淮河并列的四条大河“四渎”之一,虽然到了唐朝因流量减小、实际河道已萎缩,但仍改变不了其重要地位。
《唐会要》记载了一件事,唐太宗李世民曾问“济水甚细而尊四渎,何也?”许敬宗答:“渎之为言独也,不因余水独能赴海……济潜流屡绝,状虽微细,独而尊也。”李世民迷惑为何济水流量小却能成为四渎,许敬宗回答因其能够独立赴海,有“至清远浊”的独立品格。诗人李颀、白居易都创作诗歌歌颂“济水”的这一士大夫节操,成为了文人精神图腾。

从这一点看,“永济渠”与“济水”在诗人们中有着极为悬殊的地位,作为诗仙的李白,其创作的诗歌中“思君若济水”一句,“济水”绝非“永济渠”,而是“四渎”之一的“济水”。
如果诗里非得要提“永济渠”的话,从古人创作时引用典故、运用简称等习惯来看,也很大概率也不会用“济水”,而是“永济”“白渠”“御河”中的任意一个名字:因为如果用“永济渠”的简称,肯定不会是“济水”,因为这两个字代表的并不是永济渠,其简称只能是“永济”。至于“白渠”“御河”,可参见编修于唐朝的《元和郡县志》《通典》,这两部典籍中记载永济渠均为:“白沟本名白渠,隋炀帝导为永济渠,亦名御河。”

此外再多说一下。“济水”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中是在宋朝晚期,由于黄河改道的影响,“济水”上游入于黄河,下游河道则成为了“清河”,也就是今天的黄河山东段。“汶水”在宋末是大清河的上游,到了元明清时期,汶水又成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主要水源,其水流在汶上县南旺镇一分为二,“七分朝天子、三分下江南”,南下北上。其中北上水流在张秋镇仍与大清河也就是古济水河道发生联系,或许也由此明清时人们把“济水”和“汶水”认为同一条河了,也就造成文人在集撰唐朝李白诗集时,把原本的“思君若济水”讹为“思君若汶水”了。


三、李白还有一首诗里有“沙丘”,那就是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,兼问稚子伯禽》
这首诗创作之时,李白正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旅居,这时他离开“沙丘”已有三年之久,因为想念仍在“沙丘”的孩子“伯禽”,当听说“萧三十一”要回“鲁中”,便托其到“沙丘”看望一下稚子伯禽,送行时创作了这首诗“……高堂倚门望伯鱼,鲁中正是趋庭处。我家寄在沙丘傍,三年不归空断肠。君行既识伯禽子,应驾小车骑白羊。”

很明显,“萧三十一”去的地方是“鲁中”,去这里的时候会经过“沙丘”,看一下李白的孩子是顺路而为。虽然我们不确定李白诗中所说的“鲁中”究竟是哪个地方,但我们或许可以暂且推断位于春秋战国时鲁国的首都曲阜一带。
如果说李白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中的“沙丘”是在今天邱县香城固,那么从曲阜到这里的距离足有6、700里,这样的距离在古代算得上是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,李白让人家“萧三十一“跑这么远去看他的孩子,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。
由此可以推断出,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,兼问稚子伯禽》两首诗中的“沙丘”并非是邱县香城固,而更接近于“鲁中”,究竟在哪?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。
四、李白诗里的“沙丘”,其实已有明确记载。
按照上述推断的“鲁中”在今天山东省曲阜市一带,其西部15公里的地方是济宁市兖州区,明清时为山东兖州府滋阳县,无论是在清朝的《兖州府志》,还是《滋阳县志》,《古迹》中均记载有“沙丘”:
府志:沙丘,城东二里黑风口西。……至今地名沙堆社。县志:沙丘城,唐李白有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云:“我来竟何事,高卧沙丘城。”又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》诗云:“我家寄在沙丘旁”。唐鲁郡治瑕丘,白(指李白)久客鲁,据诗则沙丘城应在境内。
另外,1993年在兖州城东南泗河还出土了《北齐沙丘城造像残碑》,也称《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》,简称《沙丘碑》,碑文有“以大齐河清三年(564年),岁次实沉,于沙丘东城之内”。

前有北齐“沙丘碑”,后有府志、县志,均明确表明了山东济宁兖州区曾经存在过“沙丘”,其位置位于“鲁中”附近,正是“萧三十一”能够顺路、力所能及、轻而易举能够访问到的、李白的居所“沙丘”。
综上所述,邱县香城固出土的唐《万仁则墓志》中所记载的沙丘城,是隋唐沙丘县治所无误,但却并非李白诗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中的沙丘城,此沙丘应该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。
为什么在唐《万仁则墓志》中出现都是在说沙丘城,但实际上却并非是同一“沙丘”的情况呢?
这个原因或许可以从墓志撰写者耿湋身上找到。大历元年(766年),耿湋受托给万仁则撰写墓志时,是他于宝应二年(763年)进士及第后任盩屋县尉的第三年,作为朝廷命官的他,显然不可能擅自离开工作岗位,到已被藩镇割据下的沙丘城了解情况之后才开始撰写。

由于他并未到过河北,再加上缺乏精确地图指引的古人普遍性对各地地理位置不明白、不清楚(这一点从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对地名、路程描写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),而诗仙李白的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此时也已传播开来,对于在关中盆地里盩屋县的耿湋来说,可能就会想当然的把作为县治的沙丘城与与著名诗人李白所居的“沙丘”划归在一起,认为就是同一个地方了。
您认为是这样吗?欢迎在文章底部讨论。
配资知名炒股配资门户,配资炒股平台找加杠网,西安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